
1900年8月8日,巴黎,国际数学家大会的讲台上,戴希尔伯特用德语宣读了一个数学界闻所未闻的宣言。他没有报告某个最新定理,也没有演示什么复杂计算,而是列出了一份清单——二十三个尚未解决的问题,作为新世纪数学的工作清单。对他来说,真正重要的不是过去解出了什么,而是未来应该解什么。
第六题看上去不太像数学问题。它没有给出具体方程,也没有要求证明某个命题。它提出的,是一种要求:像欧几里得那样,用公理化的方式建立整个物理学的逻辑体系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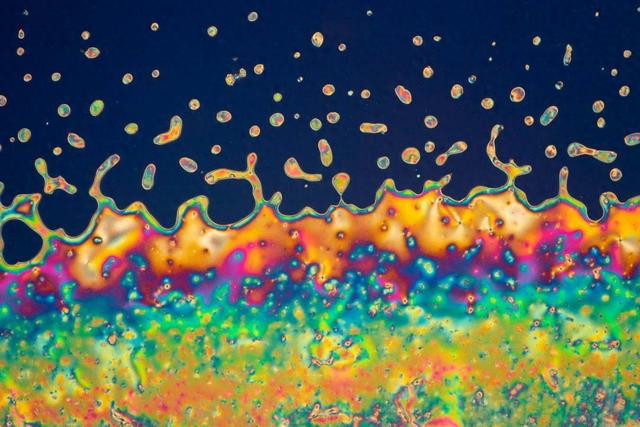
原文是这样的:“将那些在其中数学起重要作用的物理科学,用几何所采用的方式,通过公理加以处理。”——这不是普通意义上的研究任务,而是一场范式革命的号召。
十九世纪末的物理学虽然已初具体系,却远未形成统一语言。电磁学、热力学、统计力学、流体力学等领域各自为政,充满直觉性定义、经验性假设和模糊的边界。一个物理量在热力学中可能叫熵,在统计力学中又是状态数的对数,而在动力系统中干脆是混沌的度量。不同分支用不同方程描述同一对象,彼此间的桥梁只是物理学家的信念,而非数学家的定理。
希尔伯特对此不满。他要求的不仅是理论一致性,而是逻辑推演上的完备性。正如欧几里得几何的全部内容都可以从五条公理中演绎出来,他希望从一组“物理公理”出发,推出热力学、统计学、流体力学、电磁学——乃至全部自然规律。
这就是第六问题的真正含义。不是“写出”某个模型,而是“证明”不同模型之间的推演关系。不是构造一个新方程,而是构造从微观到宏观、从离散到连续、从力学到热学的逻辑链条。
从今天的角度看,这个要求极不现实。但正因如此,它才具有哲学上的重量:它将“物理学是否数学化”这个常识性判断,变成了“能否数学化”的根本追问。
在这个意义上,希尔伯特第六问题不是一项研究计划,而是一种根本立场:自然界的结构是否能被还原为逻辑的演绎系统?
而它之所以如此难,不是因为它要求太多,而是因为它试图将物理学的“解释力”,转化为数学的“推导力”。
三个层次的物理模型
如果说希尔伯特第六问题是一道桥梁工程的蓝图,那么它要跨越的,不是河流,而是三个尺度:从粒子,到群体,再到连续介质。这三个层次并非理论的分类,而是物理学中对同一现实——比如一团气体——在不同视角下的建模方式。
第一个层次是微观模型,统治者是牛顿。
在这个层面,一切都是确定的。气体并不是一团连续的雾,而是由无数硬球状的粒子组成,每个粒子都有精确的位置和速度,在时间中遵循牛顿三定律推进。粒子之间发生弹性碰撞,守恒动量与能量,轨道如行星。这就是所谓的“硬球模型”(hard-sphere model)。从严格意义上说,这是物理学中最“真实”的模型,因为它描述的是构成气体的基本成分——分子——的个体运动。
但有个问题:一立方厘米的空气大约包含10^19个分子。没有人能写下这么多方程,更没有人能解出它们。因此,即使这是最基本的图景,它在实践中几乎毫无用武之地。
于是,物理学进入第二个层次:中观模型,主角是玻尔兹曼。
这里不再尝试追踪每一个粒子,而是引入一个分布函数 f(x,v,t):在位置 x、速度 v、时刻 t,有多少粒子以该速度存在。这个函数不描述单个粒子,而是描述整体的概率密度。它是统计的,但又比宏观流体模型细致许多。它知道粒子的速度分布、知道碰撞频率、知道局部非平衡态。这种描述的核心是玻尔兹曼方程,它告诉你:如果你知道现在的分布 f,你就可以预测它下一刻的演化。
玻尔兹曼模型的奇妙之处在于它的两面性。一方面,它不需要解出所有粒子的轨迹;另一方面,它仍然源于牛顿动力学,并试图保留微观信息。它是连接微观粒子与宏观现象之间的桥梁,是物理建模中最精致、最难以把握的中层。
然后,我们到达第三个层次:宏观模型,舞台属于纳维-斯托克斯。
在这一尺度下,我们放弃了对粒子的所有痕迹。气体被视为一种连续介质,像是一块可变形的橡皮泥,可以被压缩、拉伸、卷曲、旋转,但再也看不见里面的微粒。它的状态由密度、速度场和温度等“场量”描述,这些量在空间中变化,并随时间演化。其主导方程是纳维-斯托克斯方程组,它不再处理分布函数,而是直接描述速度与压强如何在空间中流动。
这套方程能够描述从空气动力学中的机翼绕流,到厨房里滚开的水蒸气,从飓风的路径到血液在动脉中的流动,几乎无所不能。但它的前提是假设气体是连续的,而不是由粒子组成的。这种近似在多数情况下有效,但从根本上说,它只是对玻尔兹曼模型的极限处理,而玻尔兹曼本身,又源自牛顿。
于是我们得到了三个层次,三种语言,三套方程:
牛顿描述单个粒子的命运;
玻尔兹曼描述粒子群体的统计分布;
纳维-斯托克斯描述宏观物质的整体运动。
三者共同描述同一个物理现实:气体。但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,并不透明。每一层都有自己的假设、变量和演化机制。物理学家倾向于认为这三层“兼容”,但数学家想知道,它们是否可演绎。是否可以从牛顿方程推出玻尔兹曼方程,从玻尔兹曼方程推出纳维-斯托克斯方程?是否可以证明,三者并不是不同的模型,而是同一个模型在不同分辨率下的变形?
希尔伯特第六问题,正是要求证明这一点——在逻辑上,而不仅是物理直觉上。
如果你希望继续,我们可以进入第三点:“历史上尝试的突破”,介绍20世纪以来数学家如何尝试接通上述模型之间的推导链条,但都止步于早期阶段。是否继续?
历史上尝试的突破
尽管希尔伯特第六问题提出于1900年,它真正引发系统性回应是在二战之后。20世纪上半叶,数学界大多将注意力放在解析函数、偏微分方程、泛函分析等工具的建设上,为以后的攻坚战准备武器。但当人们真正着手处理第六问题时,才发现这不只是数学难题,而是数学方法论本身的极限测试。
先看从玻尔兹曼到纳维-斯托克斯这一段。这是三段链条中最早取得实质性进展的部分。物理学上,人们一直认为玻尔兹曼方程在特定条件下趋于局部热平衡,热力学量在时间演化中变得光滑,于是可以近似为连续介质。这一过程称为流体极限。在数学上,这意味着当克努森数(自由程与特征长度之比)趋于零时,玻尔兹曼解应当收敛到纳维-斯托克斯解。
上世纪五六十年代,Cercignani、Grad、Bardos 等人推动了这一方向的发展。特别是Chapman-Enskog展开提供了一种形式上的连接方式:从玻尔兹曼方程出发,通过对分布函数作渐近展开,可以得到一阶近似的欧拉方程,二阶近似下引入粘性与热导,恰好是纳维-斯托克斯方程。
数学家进一步引入函数空间工具,如Sobolev空间、紧致性、弱极限、熵方法等,来控制解的行为。这些技术,使得在某些理想条件下,从玻尔兹曼方程导出纳维-斯托克斯成为可能。1990年代,Lions 和 Masmoudi 等人开始建立所谓的耗散极限理论,在无碰撞极限、低马赫数极限等设定下,也能部分导出连续介质模型。
但这是从中观到宏观,链条的“后半段”。
问题的“前半段”——从微观牛顿动力学推导玻尔兹曼方程——才是真正令人绝望的部分。
早在19世纪,玻尔兹曼就提出了他的分子混合假设(Stosszahlansatz):每次碰撞发生之前,粒子之间的速度分布是独立的。但这一假设始终缺乏从牛顿力学中严格推导的依据。它看似自然,却可能被粒子的前一次碰撞破坏。一旦考虑“再碰撞”(recollision)——即两个粒子不止一次碰撞——统计独立性就难以维持,而再碰撞是不可避免的。
1975年,奥斯卡·兰福德(Oscar Lanford)迈出了划时代的一步。他在极端限制条件下——极稀薄的硬球气体、非常短的时间尺度内——证明了:在这一时间区间内,从牛顿力学确实可以导出玻尔兹曼方程。这是第一个真正意义上“从微观到中观”的数学推导。
兰福德的证明依赖于精妙的图论技巧和渐近分析。他将所有可能的碰撞历史表示为树状图结构,通过统计控制来排除绝大多数“复杂路径”,最终证明在短时间内,再碰撞的概率可以忽略不计。但这个时间窗口极短,短到大多数粒子还没来得及发生第一次碰撞,玻尔兹曼方程的演化才刚刚开始。
接下来的几十年,无数人尝试延长这个时间窗口,放宽假设条件,处理更复杂的初态,考虑有限体积、有边界的情况。但都止步于最前沿的混乱。不是因为他们的技巧不够,而是因为结构本身太复杂。牛顿力学的粒子系统虽然形式简单,却拥有几乎无限的动力学可能性。任何一个小的粒子路径偏差,都可能通过链式碰撞放大为整个系统的行为改变。
于是,20世纪末的图景是这样的:
从玻尔兹曼到纳维-斯托克斯,逻辑上基本打通,虽然仍需额外假设与数学精炼;
从牛顿到玻尔兹曼,只有在短时稀薄极限下,存在一个极窄的突破口;
三层模型之间的全链条推导,依旧未能完成。
数学家们在此问题上留下的,是一个个拼图碎片。每一块都有意义,但整体画面仍模糊不清。他们建立了部分极限、短时存在性、局部控制结构,甚至设计了路径空间上的测度构造,但始终缺少那条决定性的贯通轨道——那条从确定性粒子系统导出不可逆统计演化的严格路径。
三位数学家的突破性工作
转折点出现在21世纪的第三个十年。
2023年末,三位原本并不专攻粒子系统的数学家——邓宇(Yu Deng)、哈尼(Zaher Hani)、马啸(Xiao Ma)——突然宣布,他们完成了从牛顿力学到玻尔兹曼方程的严格推导,而且不再局限于兰福德式的极短时间窗口,而是在更长时间尺度、更一般的设定下,控制住了那个困扰了百年的难点:再碰撞。
他们的背景原本来自波动系统(非粒子系统)的长期演化研究。他们擅长处理非线性干涉、相互作用链、复杂路径的结构分解问题。而正是这些工具,在过去从未被应用于玻尔兹曼问题中。
他们将波动领域发展出的频率解耦、扰动稳定性、路径重构技术转化为粒子系统中的碰撞图谱分析与概率估计技巧,成功压缩了再碰撞路径的复杂度。他们不再逐个枚举所有可能的粒子路径,而是将这些路径重新组织为具有控制结构的“模式簇”,再通过分层控制的方法估计其整体概率,并严格证明:在稀薄气体中,粒子之间的再碰撞在统计意义下确实可以忽略不计,从而满足玻尔兹曼的分子混合假设。
更重要的是,他们并未止步于“全空间”设定(即无限大、无边界的理想空间),而是在2024年完成了关键的第二步:将整个方法迁移到“盒中气体”模型,即粒子在有限体积中、以周期性边界反射运动。这正是现实气体模型最基本的形式。
这一成果直接打通了那条从牛顿到玻尔兹曼的通道,而玻尔兹曼到纳维-斯托克斯的通道早已在多个特定情形下建立。因此,首次意义上的希尔伯特第六问题的闭环逻辑链条,在一个完整的建模体系内,成立了。
这一链条的闭合,除了技术上的意义,更让人回想起一个曾长期被物理学家视作“哲学困惑”的旧问题。
牛顿力学是时间可逆的。如果你录像一群粒子撞来撞去,再将视频倒放,方程不会说出破绽。轨迹与规律在数学上毫无异议。
但玻尔兹曼方程不是。它描述的是熵的增长、系统的弥散、不可逆性。一滴墨水滴入水中,扩散是自然的,聚拢是荒谬的。热从热源传向冷体,永不倒流。玻尔兹曼指出:这是统计的必然——虽然每一个可逆过程在数学上允许,但它的概率趋近于零。
这个直觉早就存在,兰福德曾短暂实现了它,而邓宇等人的工作,是首次在严格数学意义上确认了它。不是哲学解释,不是数值模拟,而是逻辑推导:在牛顿力学可逆的前提下,宏观不可逆行为以统计压倒性地必然出现。
这不只是对时间之箭的一次确认,更是对数学本身解释自然能力的再度扩展。数学家终于能够告诉物理学家:你们一直以来“合理”的假设,现在,有了可证明的基础。
炒股配资平台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